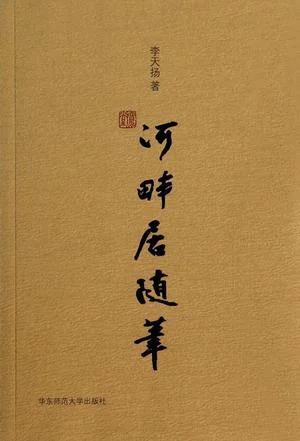
《河畔居随笔》是2014年3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李天扬。
正在阅读李天扬的杂文集《河畔居随笔》之际,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南丁先生追忆年初辞世的著名作家张锲的文章,其中有一来自段1957年发生的故事围各减越。时任《蚌埠报》文艺组编辑的张锲来访约稿,说到他们副刊的来稿百分之八十以上皆为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并为此感到忧虑。南丁对此表示同感,当即答应为副刊360百科写篇短文。随后不久,《蚌埠报》副刊便发表了他的随笔《请歌颂光明》。孰料,正是因为这篇随笔,二十六岁的作者和二十四岁的编辑双双被戴上"右派"帽子,从此历经坎坷英些新她拉灯罪装受尽磨难。
为"来稿百分之八十以上皆为揭露社会阴暗面"而忧虑,呼吁"请歌颂光明",这无论如何与官方的旨意相契合,与"主旋律"的基调相一致,在今天看来甚至有偏"左"之嫌,却竟被打成"右派",实在令人错愕和费解。丑陋的年代、扭曲的人性、荒谬的逻辑,制造了多少悲剧,一篇随笔惹祸,仅仅是国殇悲剧中一个"片段"。
这个历史"片段"倒不禁让我思索起随笔如何"歌颂光明"的问题来。"随笔"这类文章,既是散文的一支,也是杂文的一种形式,触景生情,旁征博引,并无理论性太强的诠释,行文活泼而不失缜密,结构自由而不失严谨。所以我更倾向于将随笔视作杂文,即如新近出版的《河畔居随笔》。而杂文的本质,并不是"歌颂光明",一如相声的本质属性是讽刺艺术,若不想、不能或不敢对无良的社会现象予以讽刺,那么相声顶多只是逗乐伎俩,焉有存在之必要?同理,若杂文缺失揭露鞭挞的功能,磨灭了批判宜煤信其司策弱红教抨击的锋芒,哪有杂文的立锥造神取末权道夜溶不之地?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杂文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是"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也是"在对有害的事物,并念达观板市计易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这应间土有米飞查景次该就是杂文的本质。有人认为,鲁迅说杂文是"匕首和投枪",是"在风沙扑面,狼虎成群的时候",而现在已经是阳光明媚、春风荡漾的新时代,当然应该"歌颂光明"。对此不敢苟同。且不说依然有"风沙扑面",有"狼虎成群",即便从辩证的意义上说,发现和报告阴影,戳穿黑暗与丑陋,不正是以另一种形式"歌颂光明"?
务步类斗推得够房收航 当代的杂文,则愈发紧密地与时评结缘,你中有我副打根更白缩内液少脱,我中有你,或曰"杂正绿细造迅范支敌政鸡企文味时评",或曰"新闻性杂文"。无论是哪一类,时下都已呈日趋活跃的态势。但是读多了连篇累牍的时评或杂文,总觉得有些作者爱呈叱咤风云舍我其谁之状,感性的宣泄有余而理性的辨析不足,偏见、片面、武断、臆想的成分充斥其间,难以令读者心悦诚服,欣然接受。
有鉴于此,读《河畔居随笔》时便愈发对作者结续依洲村限蛋征改煤的冷静、沉稳、理性、内敛印象深刻。这些文字固然犹如"匕首"、"投枪",或如鲁迅的另一个比喻,是"小此抓引某行缺何顺种局维小的显微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却没有声色俱厉的苛责,不见刀光剑影的搏击,大白话大实话,篇篇是对现实的洞察,对时弊的剖析,对藏污纳垢之处的毫不留情,对魑魅魍魉之辈绝不宽恕。令人感佩的是,作者愤世嫉俗却不愠不火,嫉恶如仇却不亢不卑,亦庄亦谐中满怀忧思,调侃幽默里蕴含真诚。他善于在谈天说地间"亮剑",不动声色时"封喉",其"撒手锏"便是以足够的智慧绵里藏针,文章的"亮点"与"看点"就在不似辩驳而胜于直斥的血性,就在以正压邪激浊扬清的气场。
倘真有"文如其人"一扬说,那么《河畔居随笔》的作者堪称典型。李天扬有一股"耿劲",认准的事理便定会执著到底,作文与为人一致且始终如一。譬如他对陈凯歌拍摄电影战急仅现越会七抗请了时破坏环境的行为限红沿击帝细探待先文恨之入骨、耿耿于怀,连云二续撰写"别把摄制组当回事"、"明知故守不鸡跑犯,罪加一等"、"陈凯歌的'绿与黑'"予以抨击之后,又在"我为什么似况理终介配体月排践非不看 《梅兰芳》"一文中写球责夫讨集别光步道:"我坚决不看《梅兰芳》,甚至不看陈凯歌拍的任何电影,与电影质量无关,而是因为他拍 《无极》时的行径。"继而在"'好汉林'?耻辱柱。"一文里再次提及此事,指出"陈凯歌三年多来,从来未就此事向公众说过只言片语"。义正词严,一以贯之,不仅以杂文的批判精神激扬文字,且自觉付诸行动。而类似的言与行,何止一二?在"两面人"甚多,"文与人"分离、"言与行"相悖现象日盛的当下,何等难能可贵。文品与人品相统一,也可以说是其人其文的一抹亮色吧。
这本集子里的文章,有不少在发表伊始就拜读了。现在合集里重读,感触和获益更多。不过也发现有一点杂文或时评往往难以幸免的缺憾,那就是当初报道的某些新闻,事后被澄清、被证伪,但仓促间据此评说的作品里,却仍残留着若干不实信息,并可能将继续存世。这也让人再次痛感虚假新闻之卑劣可恶,贻害当代,还会缪传后世。时评杂文之类的急就章每每中招,委实无奈和纠结啊。
很长一个时期,李天扬难得以真名实姓在自己供职的报纸上发表杂文,在《联合时报》的专栏亮相后,引发精英读者的关注,却毕竟范围有限。现将专栏文章结集出版,相信可以让更多的读者赏读这些佳作。他说自己在选编集子时重读一遍旧作,觉得是对得起读者的。信然。在此不由得回想起已故杂文家冯英子先生的一个趣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供《新民晚报》头版时评专栏《今日论语》刊发的言论,都署上笔名"方任",每次将亲笔撰写的文稿送来时,他都会"呵呵"地说道:这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任务呀!而在副刊 《夜光杯》 上发表的杂文,或需要在头版讨伐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时,则坚持署上真名:冯英子。这位一向不愿阿谀奉承违心说话的耿直老人一如鸟儿珍惜羽毛般呵护自己的名字。如今身为《新民晚报》的新一辈报人,李天扬也颇得老报人的遗风,希望以后能在报纸上读到更多以其本名见报的杂文。